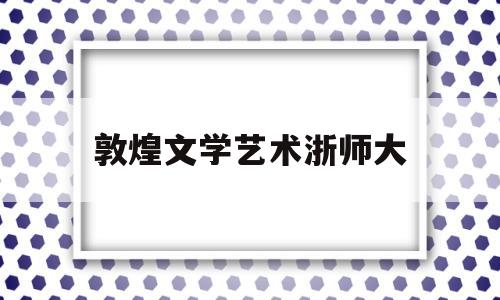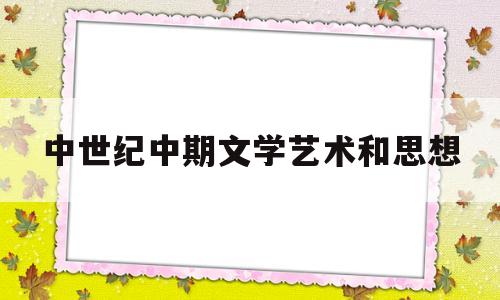古远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2016年的台湾文学事件
文·古远清
(《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文学事件,是指文学现象或文学论战甚至作家的去世超出了文学范围,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兼具一些动态的新闻价值,特殊者甚至成为社会、政情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它虽然建立在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基础上,但其理论重心已由文学生产维度、读者阐释维度向意识形态方面转化。
“台湾文学系”:无可奈何花落去
继2015年淡水“真理大学台湾语言学系”停办后,今年夏天台中“中山医学大学台湾语文系”送走最后一批应届结业生,这象征着该系又正式倒闭,《文学台湾》等媒体最近由此展开讨论“台湾文学系是否将逐一关门”这一话题。其中《联合新闻网》的标题为《台文系倒闭,象征本土化的黄粱一梦?》。有网民称,“全世界都在学中文,只有这群夜郎在自豪”。这里说的“夜郎”,是指部分“台湾文学系”的教师放弃中文而提倡什么“台文”,即用中国方言闽南话和客家话写作。一些网民对办“台湾文学系”很不以为然,认为“台文系误人后辈,教出来的‘太阳花’只会闹事”。还有人直言,以政治目标伪装文化,又没有足够的内在学术力量去支撑,只能获得“假鬼假怪”——即不是中国人而是与中国无关的所谓“台湾人”。
研究台湾文学,本应是大学中文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实行白色恐怖,不许讲授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再加上中文系长期以来厚古薄今,背上了国学的沉重包袱,致使许多人并不认为台湾有文学,或认为有文学但成就很小,完全不值得研究,这便形成研究本地文学没有学术地位的偏见,使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台湾文学一直无法进入高校讲坛。尤其是在1970年以前,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的假面具还未揭露时,如果有谁提“台湾文学”,会被认为不赞同“中华民国文学”,就会被安全部门过问,因而各大学根本不可能设立台湾文学课程。直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80年代,寻访台湾文化根脉的呼声高涨和本土思潮迅速占领各种阵地之际,情况才有所改变:1997年,淡水工商管理学院(现为真理大学)排除阻力终于成立了全岛第一所“台湾文学系”。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后,在本土化思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台湾文学系”遍地开花,近20多所大学设立了18个由“台湾文学”或“台湾语文”、“台湾文化”命名的学系及其孪生兄弟“台湾文学研究所”或“台湾文化研究所”、“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
尽管从南到北彼此呼应建立“台湾文学系”及“台湾文学研究所”,给人印象是势不可挡,但仍然有人不断提出下列疑问:“台湾有文学吗?即使有,可以设系或值得设系吗?”、“台湾文学够格成立一门学科吗?教些什么呢?师资在哪里?”还有人认为:“台湾文学只有三百年,而中国文学有五千年,台湾文学作为选修课开还可以,单独设系是人为的拔高”。的确,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并未事先从学理上进行充分论证。这种由政治催生学科的做法,说明“台湾文学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受政治主宰,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的“羁绊”,这将造成台湾大学生不认同中国文学,并在族群和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偏差。
用平常心看,无论是“台湾文学系”还是“台湾文学研究所”的老师和学生,主张台湾“独立”的并不占多数,即使是有分离主义大本营之称的成功大学“台文系”的部分老师,仍把白先勇、张爱玲、余光中等属中国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当作台湾文学的主流来处理。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所还开设有“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从白先勇到郭松棻60年代现代小说家作品”、“现代诗”、“现代散文”、“后殖民文学选读”等课程。众多师生更没有明确表态:中文系应与“外国文学系”合并。这也就不难理解“高雄大学”创校时,拒不成立“台湾文学系”,宁愿让“中国文学系”成为亚洲汉学研究中心。可当下在“去中国化”的思潮引导下,“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某些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也正是这种违反学术建设要求的原因,导致真正叫“台湾文学系”的全岛只有三所:北部的真理大学、中部的静宜大学、南部的成功大学,其他院校鉴于“台湾文学系”的牌子市场前景不看好,便不断的更名,如改为“乡土文化学系”、“台湾语文与传播学学系”、“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学系”等。当下办得最成功的为成功大学“台文系”,设有博士班、硕士班、大学部,若顺利的话,大概可以读十年以上。只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台文系”学生毕业后到底出来要做什么?有人在网上调侃说:“可加入民进党成为党工从政、举旗子、发便当、订游览车,再不行从事民进党主办的地下电台卖药兼宣扬台独理念给人洗脑。”把“台湾文学系”等同于“台独(台毒)养成班”,显然是以偏概全,“台湾文学系”目前还是学术和教学单位,但的确有一些数典忘祖的老师在任教,使“台湾文学系”难于被人尊崇,正如不少人批评的那样:“台湾文学系”不过是一个政治主张的文化表现,其自身学术力量严重不足,像《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几乎是靠对岸学者所撰写,有些人一边批评大陆学者著作,一边又在论文中或在课堂上加以正面引用。
的确,说着中国话用着中国字,可打出的是“台湾语文系”的招牌,这使人感到是一种悖论。“台湾文学系”或“台湾语文系”的设立宗旨,并不单纯是“松动”中国文学的一统天下,而是为了与中国文学、中国语文分庭抗礼。只要“台湾文学系”或“台湾语文系”一成立,各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大学国文》不是减少就是被废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台湾文学课程,这样使学生减少了接触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机会。曾任“共生音乐节”发起人的蓝士博认为,现在“台文系”的最大挑战,便是台湾文学研究体制与国民教育的极度脱钩。当体制内外的“循环”与“再生产”无法完成,对内无法整合分工,对外无法争取空间、资源,连有别于“中国文学系”的文化底蕴都无法完成,“台文系”诞生的“20年终将只会是黄粱一梦”。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离开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将只会是黄粱一梦。此话虽然说得尖刻,但事实本来如此,“台湾文学系”早已成为零散于各大专院校的“弱小科系”:在硬体与软体设施方面,“台湾文学系”始终比不上中文系,至于全岛43所院校所设立的中文系及研究所建立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台湾文学系”师生即使再努力20年、30年,也是达不到的。
这场“台湾文学系是否将逐一关门”的讨论,有利于中华文化的维护和提升。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久前的真理大学“台湾语文系”和当下的中山医科大学“台湾语文系”寿终正寝,是理所当然。因为“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20年来一直找不到定位,一些“独派”学者将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学”加以排挤,并打算将其“挤”到外文系里去。这就牵涉到“台湾文学系”是否应与中国文学切割,还是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发展这一大是大非问题。关于后者,明确主张的人虽然不多,但多数人认为“台湾文学系”与中国文学“断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且不说台湾文学的产生系祖国大陆文人沈光文带去的火种所点燃,单说当下的台湾文学创作,哪一个作家没受过中国文学的哺育?更何况两岸作家同根同种同文,有如余光中所说的“吃的是米饭,用的是筷子,过的是中秋,写的是中文”。可“台湾文学系”部分“基本教义派”,认为台湾文学不是日本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学,还鼓吹什么“台湾文学主权在台湾”。以这种思想办“台湾文学系”,向学生灌输“中国文学”是“敌国文学”,台湾文学才是“本国”文学的观念,难道不是误人子弟?
众所周知,让台湾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是根本不可能的。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决不像有人说的有如“英、美文学之间的关系”。两岸不是“两国”,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像有人鼓吹那样唾弃中文而改用什么“台文”写作,可闽南话大部分有音无字,书写起来困难,作者写得辛苦,读者读起来更辛苦,难怪黄春明在一次演讲中说:爱台湾不等于讲闽南话,大家应该用中文来写作,以方便与读者沟通。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蒋为文副教授,认为用中文写作属“卖台”的可耻行为,便在黄春明演讲现场举牌抗议,可他抗议黄春明的大字报全部用中文写就,而且还的三个简化字,这真是最大的黑色幽默。退一步说,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后作家们仍用英文写作,何“可耻”之有?更何况台湾“独立”根本就不可能。须知,民进党的“台独”党章也全是用中文所写,这有如蒋为文和蒋介石同姓,他肯定是中国人一样。
除“台湾文学系”是分离主义思潮下的产物,促使办学方向走入死胡同外,还在于不少院校的“台湾文学系”与中国文学系始终处于对立关系,而不是一种互补关系。在某些大专院校,多认“小乡土”的“台湾文学系”与多认“大乡土”的“中国文学系”关系异常紧张,想进行对话都不太可能。此外,“台湾文学系”始终未能走出学院围墙,未能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承认。他们不承认也有道理,因为“台湾文学系”某些人所主张的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社会上许多人士均不以为然。须知,国民党过去打压本土文学固然是大错特错,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让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母体,甚至主张用“台语”写作才是所谓纯正的台湾文学。这是自我剪裁、自我矮化、自我割裂、自我村落化的行为。如果写台湾文学史将用北京话写作的余光中、陈映真、白先勇等人用“减法”去掉,那台湾文学史只剩下三两页了。
关于“台湾文学系是否将逐一关门”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台湾各大专院校“台湾文学系”目前不可能都像中山医科大学“台湾语文系”一样走向死亡但会逐渐式微,或者说多数“台湾文学系”仍将在困境中苦撑,至于“台湾文学研究所”,其命运可能要好一些。须知,改名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关键是学科定位要准确,比如从文学教育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设立“台湾文学系”而是设立台湾文学专业,它有利于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日文系、历史系的科际整合,有助于培养台湾文学研究人才,有利于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台湾地区现代文学分流,有助于台湾文学研究从边缘走向专业,使台湾文学研究、创作与教学成为文学院发展的一大特色。即是说,“台湾文学系”如不单独设立,而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专业来耕耘,让台湾文学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学的母体,这样台湾文学的教育才有正确的方向,才不会像真理大学“台湾语言学系”和中山医科大学“台湾语文系”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因师资严重不足和招不到学生而关门大吉。
超级“战神”陈映真告别文坛2016年11月22日去世的坚强民族主义战士陈映真,其文学理论最为人熟知的是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他历来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负民族大义,手著家国文章”的陈映真,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不断和一些島内外的分离主义者展开论争,因而有超级“战神”之称。
陈映真
后来成了“台独”派文学宗师的叶石涛,是陈映真的一个重要对手。1977年5月,叶石涛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提出“台湾意识”这一概念,并认为只有用这种意识写的作品,才能称为乡土文学。陈映真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中,认为“台湾意识”这种说法很暧昧而不易理解。在陈映真看来,三百多年的台湾历史应纳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脉络里。日据时代以前的台湾社会,与近代民族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没有本质区别。“台湾立场”在最初只有地理学上的意义,具体到台湾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如果说,台湾文学是以“台湾意识”写成的,那“台湾意识”也不过是“中国意识”之一种。既然如此,就不能把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和夸大,因为说到底,台湾文学不过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
陈映真和一些论者的争鸣,是一种诠释权的争夺。1984年1月,在联合国工作的殷惠敏用渔父的笔名写了一篇评论陈映真小说集《云》以及《铃铛花》、《山路》的长文《愤怒的云——剖析陈映真小说》,在《中国时报》发表,后引来陈映真措词强硬的《“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评渔父的发展理论》反弹。两人的争论集中在“发展理论”、“依赖理论”及第三世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优缺方面。陈映真认为,对方谈文学是个幌子,谈有关政治理论问题才是真的。对方是为新殖民主义辩护,且密告和打击“民族主义者”,宣扬先进资本主义的光荣和繁华,是买办知识分子的言论,是一种虚无、犬儒、堕落的行为。这种指责也暗含原先认同社会主义后来转向的陈映真早年密友刘大任在内。
陈映真参与的论战多为统“独”论辩,典型的有1995年发生的“三陈会战”,即由陈昭瑛、陈芳明、陈映真参与的新一轮论战在台北进行。不论陈昭瑛的文章《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如何以学术探讨的面目出现,一旦以“本土化运动”作论述对象,就会牵涉到敏感话题。当作者站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诠释台湾文学的发展时,便难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带有很强的挑战性。其挑战对象为以中国相对的立场建构台湾文学的独立史观。陈昭瑛在批判陈芳明观点的同时,提出了不少理论盲点质疑统派领袖人物陈映真。陈映真则对陈昭瑛将反日、反西化和反中国的“本土化”列为“文化史”上的先后分期并相提并论,提出质疑与商榷,但这“三陈”会战并不等于有第三势力介入。
陈映真参加的论争最有名的是发生在新世纪初的“双陈”大战。陈芳明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映真曾任中国统一联盟创会主席和劳工党核心成员。即一个是独派“理论家”,一位是统派的思想家。他们有关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的论争,文章均长达万言以上。和70年代后期发生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一样,这是一场以文学为名的意识形态前哨战。“双陈”争论的主要不是台湾文学史应如何编写、如何分期这一类的纯学术问题,而是争论台湾到底属何种社会性质、台湾应朝统一方向还是走台独路线这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陈映真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坚持始终如一,其态度令人动容,也令人钦佩。他拒绝接受任何冠上“台湾”之名的文学奖(按:这有点“过于执”),或打着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旗号的选集选用他的作品。1980年代末,钟肇政受“前卫出版社”之托,出任《台湾作家全集》编委会总召集人。鉴于出版社和主持人有严重的台独倾向,陈映真刻意“缺席”,黄春明、王祯和、白先勇等人以版权问题为托词婉拒。“全集”于1991年出版。钟肇政后来表示,“我是编辑委员会的总召集人,有些明明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作家,可是他不同意把他的作品提供出来参加《台湾作家全集》里面,他认为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学而不是台湾文学,那我们就不能勉强他。”关于陈映真在台湾出版的多种文选中的“缺席”现象,均不是主事者没有考虑陈氏作品的入选,而是因为陈映真觉得主事者或出版社有“台独”倾向,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出现在绿色文学机构或出版单位中。对祖国大陆出版他的作品,他则从不“婉拒”或“坚拒”。
既反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台独”的陈映真,多次险遭封杀。1968年5月,陈映真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前夕,因“民主台湾联盟”案被“警总”保安总处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书册及为共党宣传”等罪名逮捕。陈映真被捕前的旧稿《永恒的大地》于1970年2月由尉天骢以花名秋彬刊登于《文学季刊》。1975年10月,远景出版社出版还在狱中的陈映真小说《将军族》。此书为1968年前陈氏所写的各种短篇小说,许多作品弥漫着惨绿的色调,表现出苦闷中的小知识分子浓厚的伤感情绪。作品中不少的主人公系大陆移民,作者写出他们的苍桑传奇,并表现了外省人和当地人的密切关系。1976年初,“警总”正式查禁《将军族》。1982年,胡秋原主编的《中华杂志》要求《中央日报》刊登出版广告,因目录中有陈映真的名字,被拒绝刊出。理由是“陈映真的名字不能登《中央日报》,昨天某书店的广告因有陈映真的名字已被删除。”1984年2月,《中华杂志》再次要求《中央日报》刊登该月目录预告,虽然刊出了,但《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陈映真主讲》一行全被删去。1984年3月10—12日,《中央日报》大幅刊载沈登恩主持的远景出版公司新书广告,内有《山路/陈映真著》、《历史的孤儿,孤儿的历史/陈映真著》,刊登前报社要求删去这两条,后因先付了广告费而没有删去。左翼人士钱江潮为此写了《致〈中央日报〉社长姚朋先生公开信》,强烈抗议姚朋企图封杀陈映真的做法。
左右开弓、骁勇善战的陈映真,其论战的“文学台独”对象除岛内的叶石涛、陈芳明外,另有法国和日本的作家、学者。
2001年初,高行健到台湾访问两周,演讲热潮燃烧到台南各地,《中央日报》等11家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当灵山遇到灵肉》,出版社也赶印了10多万本《灵山》,高氏及其作品成了许多大中学生智力测验之外另一寒假梦魇。对此现象,连力捧高行健的马森也认为,台湾读者抢购此书“不是爱读文学,也不是看懂了《灵山》,而是崇拜名人,追赶时髦!”他得奖不少人认为是政治因素起作用,其作品“在正常的文学市场机制下,金石堂排行榜就排到一百名也未必有他”。连邀请他访台的龙应台也认为其得奖不过是“一群有品味有经验的人,向读者推荐一位值得认识的作者”。陈映真则对高行健“没有主义”的主张发出猛烈抨击,认为高氏放弃民族认同,否定文学的社会性,这种“逃亡有理论”是唯心和个人主义的。“独派”作家发出另外一种声音:这位号称“中国文化就在我身上”的作家,所体现的是“外国”文化,与台湾毫不相干。但有许多人认为,高行健得奖毕竟为华文文学走向世界开了先例,他其实是在代鲁迅、林语堂、沈从文、艾青等人领奖。
在东京大学任教的藤井省三,其“独派”观点较为隐蔽,即使这样,也被陈映真所识破。
由于陈映真的观点深得人心,故岛内有一些人为陈映真的理想辩护。2004年9月,学者邱贵玲因为“云门舞集”编的《陈映真·风景》舞蹈卖座率甚低而发表《山路到不了的乌托邦》,结果引来杨渡、梁英华、汪立峡在《新新闻》杂志以及李良、胡承渝等人在“人间网”发表文章反弹,他们均为陈映真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其行为作激烈辩护,辩论期间陈映真从头至尾未置一词。
又如2008年初春,台湾文学馆为提升国民素质而推出《阅读台湾,人文100》系列活动,总共提出104本好书。该馆当时由绿营人士主持,故不但统派陈映真的作品没有入选,连外省作家余光中、朱西宁也都缺席。这引发台湾文化界的非议,如《中国时报》发表《书单色彩偏独,观点过于狭隘》的文章加以批评。绿营的陈明成也认为在没有“版权”或“侵权”顾虑的情况下,“无视文学发展历史来剔除陈映真等人的创作,实属不妥。”
在台湾,像这样不断向分离主义者展开进攻战的超级“战神”陈映真,还真难找到第二人。当下台湾迷失了方向,缺乏历史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让陈映真的思想、理想与战斗激情在宝岛传承,才能摆脱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制,重新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大方向。陈义芝说得好:“陈映真是台湾的良心,因为他无惧于少数,无惧于孤独,在庸俗浅薄的社会里坚持价值与理念,令人钦佩”。
注:囿于篇幅之故,本文第二部分“‘台湾文学'馆馆长人选之争”和第三部分“《湾生回家》作者造假引发的风波”及注释略,全文请参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第160-166页。